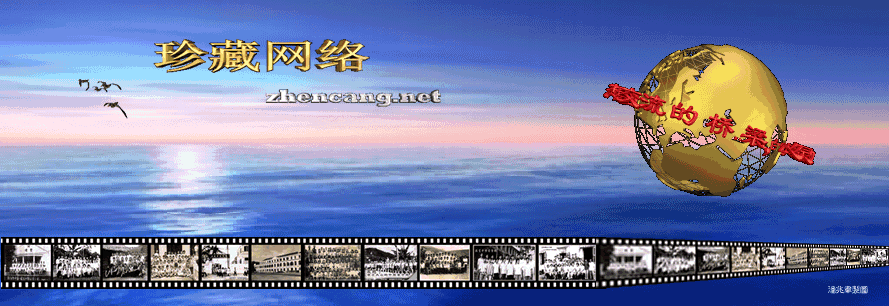
雷德侯:“万物”蕴藏中国生机
(来自瞭望)
雷德侯:“万物”蕴藏中国生机
“我不太清楚一百年以后中国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一百年以后,中国人还在写汉字,写汉字的文化一定是稳定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在汉学研究中,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对一组数据产生了浓厚兴趣——
1608年,荷兰人向中国订购了108200件瓷器。1644年,这个数字上升至355800件;
17世纪90年代,巴达维亚的瓷器经销商每年接受的中国出货为200万件瓷器;
1756年,东印度公司的六艘船到达广州,每艘船带回15万件中国瓷器;
17至18世纪,中国外销瓷产量达数亿件之巨。
显然,这些数据反映的已不仅仅是中国瓷器在技术与设计上的优势。彼时,面对欧洲的“狮口大开口”,中国皆能瞬间满足,如此大规模的生产是如何完成的?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执教的雷德侯决意一探究竟。他带着学生来到了中国,在“瓷都”景德镇,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场景,他找到了探索的路径。
终于,他理解了中国的那句古老哲言——“一法得道,变法万千”。
规模化生产的秘密
景德镇是前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工业中心,现在仍日产百万件以上的瓷器。
“一个难忘的下午,我们钦佩地观察着陶工们操作的非凡速度与灵巧。”雷德侯记录道,“他们揉捏陶泥,使之成为圆柱形,割下一个个圆盘,将其成型为一只只杯子;再以各色釉料修饰、烧制,而且出窑后又在釉色上施加更多的描画。”
次日,雷德侯带着学生到当地的一家面馆用早餐,被眼前的场面震住了——厨师们熟练地揉捏着几乎与陶泥一般软硬的面团,将其搓成圆柱状,再切薄片,然后添加各种蔬菜馅做成包子。蒸好出锅之后,还要在包子上点缀少许五颜六色的辅料。
包子的烹制与瓷器的生产是如此相似,各道工序井然,皆以流水线般的速度完成。
更令雷德侯惊叹的是,中国的餐馆通常有百种以上的菜肴被列于菜单之上,而且通常在客人叫菜之后几分钟内就将成品呈上桌面,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
他发现,其中的秘密,就在于许多菜品都有标准搭配:蘑菇竹笋炒肉、蘑菇豆芽炒肉、蘑菇竹笋炒鸡丁、蘑菇豆芽炒鸡丁、蘑菇竹笋烧鸭块,如此等等。
而汉字也是这样。“它也有标准的搭配,偏旁部首等的组合变化多端,奉行的却是同一原则。”来北京讲学的雷德侯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初涉汉学之门时,他曾陷入“苦海”,“我先是学了一百个汉字,真是很辛苦!一度想放弃,又很不甘心。”后来,他理解了汉字的“标配”,窍门洞开。
今日通行的汉字是2000多年前秦灭六国之后,规范统一形成的。彼时,秦始皇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中之一,就是其陵区之内,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陶俑组成的军阵——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武士俑平均身高1.80米左右,最高的1.90米以上,陶马高1.72米,长2.03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
当年制作这个军阵所耗用的时间,如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始,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逝世为终,共计11年,平均一年要制作700余件。显然,如果像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那样,秦朝的工匠是不可能完成如此浩大工程的。
其中的奥妙,也与汉字一样——拥有一套“标配”:每个站立的武士俑重量在150公斤和200公斤左右,一般主要由七部分组成,即足踏板,双足、外衣下的双腿,躯干、双臂,双手和头部。陶工先分别塑造这些单独的部分,然后再把它们组装在一起。
雷德侯发现,此类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在中国拥有漫长历史——
1960年10月至1961年5月,考古学家在山西侯马发掘了一处东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厂,出土3万多片陶范,它们有的能够按照一定的范式组合——像后来中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那样——形成大规模浇铸青铜器的型范。
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华先人即已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陶器,分工协作已经开始。
“当亨利·福特为1947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大规模生产’的条目之时,他将其定义为‘对应于具动力、精确、经济、系统、持续、速度,还有循环复制之原则的制造业的项目’。”雷德侯说,“除去动力之外,因为这必须归之于机器的动力,福特的原则或可应用于商代的工厂。”
“世界工厂”的历史注脚
雷德侯试图找一个术语来概括他的上述发现,他想到了儿时的拼版游戏——每一块单独的图版上,或是山峰、楼阁、屋舍、树木、马车、骑马人,地平线始终严格地通过其中点横贯左右,因此,这些图版能够组成层出不穷的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连绵不断的地平线保证了构图的清晰明了。
在德语中,这类拼版游戏被称为“移换道具”,可在英语中不存在与之同义的精确对应词。最终,雷德侯在英文书写时,采用了“module”(模件)一词。
“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件体系从事工作,并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雷德侯说,“他们在语言、文学、哲学,还有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的艺术之中,都应用了模件体系。确实,模件体系的发明看来完全合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1999年,雷德侯完成《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下称《万物》)一书,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汉学界的大师级地位。在这本书中,他从汉字、青铜器、丝绸、陶瓷、漆器、建筑、印刷术、绘画等多个方面,带领读者作了一次深刻的中国文化之旅,揭示了中国人是在一个多么复杂的体系之中,生产出成批的艺术品,这个体系又如何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宇宙观。
2005年,《万物》由北京三联书店印出中文版,并连续再版,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这本书为今日之中国何以崛起为“世界工厂”写下了历史的注脚。
“专业人员与多面手的二分法似乎是中国社会史中的永恒旋律。”雷德侯在书中写道,商代青铜器制造是一个二分法的早期例证,即一边是从事具体工作的专业人员,一边是监督工匠并对其下达任务的多面手。“在现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充当多面手,指导着专家们如何工作。”
雷德侯还考证了中国的规模化生产经验对欧洲工业革命的影响——
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神父殷弘绪前往景德镇传教,他心中怀着的正是雷德侯式的疑问。殷弘绪告诉景德镇陶工,上帝用泥土塑造了第一个人。这收获了奇效,陶工中的天主教皈依者为殷弘绪提供了资料,后者对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进行了细致观察。
1712年和1722年,殷弘绪写下两封讲述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长信,准确描述了如何使用模子来统一规格并复制各种器形,大型瓷器如何由预制的部件组合而成,以及陶工与画工的分工协作。这两封信被收入耶稣会士杜赫德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纪述》之中,迅速被译为多国文字。
“殷弘绪教士写那两封信之际,正是强悍者奥古斯特在迈森建立欧洲首家瓷厂的时候。这应该不是巧合,正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建立了国营工厂,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那时,欧洲人很钦佩中国,希望向中国学习。”雷德侯指出,1769年,韦奇伍德在英国斯塔福德建立了欧洲第一条贯彻工厂制度并全面实行劳动分工的瓷器生产线,在这家工厂里,每名工人都必须是专精某道生产工序的行家里手,这在当时是非常革命的观念,而韦奇伍德的灵感正来源于他对殷弘绪书简的阅读。
雷德侯说,如果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的范例对西方现代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影响,远远超乎世人的想象”。
文化差异其来有自
“生产丝绸,一个人是干不了的,生产水稻也是这样,这需要分工,需要大规模生产,需要大家都参加,这个非常了不起!”雷德侯对本刊记者说。
“这样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在中国出现得比西方早?”本刊记者问。
“这可能跟吃饭的方式相关。”雷德侯答,“中国比较早用陶器,在陶器里面放米,放可以吃的东西,再把它做热。而西方不是这样,古罗马人是把面包放在石头上加热。”
他认为,陶器的制作使模件化生产在中国流行,这对社会的组织方式也产生巨大影响。“建造秦始皇的陵墓,据《史记》记载,有几十万人参加,如果几十万人在一起工作,他们早上、中午、晚上都应该吃饭,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谁做这个菜?怎么做?一定是分工协作的。”
他以中国的梁架结构建筑,提供了一个模件化社会的隐喻:所有的斗和栱都是分别成型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假如有一个构件没有完好地安装,不利的后果将会加剧。如果每一个部件都完美地结合,岌岌可危的建筑物也会具有令人惊异的抗震力。
“模件体系的实际应用也必然要求付出巨大的牺牲。”雷德侯说,其中就包括“西方人认定为人类权利的某些方面”。他的研究促使人思考:东西方文化差异,其来有自。
1942年,雷德侯出生于慕尼黑。1969年,他以《清代的篆书》获得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学位。1968年,雷德侯到中国台湾学习,很想访问中国大陆,可大陆正值“文革”,他未能成行。他就跑到香港,那里有一个地方可以眺望中国内地。
“当时只有一种可能性,”他对本刊记者说,“巴基斯坦有一家航空公司飞日本,会在北京停留一个晚上,我一直想坐它,这样,我就能在北京待上一个晚上。可是,他们说我不能离开机场!”
1977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北京。“大家都穿蓝颜色的衣服,很有意思。”他回忆道,“那个时候,没有人偷东西,根本没有。”
“伏尔泰曾经评论道,东方各民族昔日曾称雄一时,但是西方人追回了失去的时间,成为地球上的优胜者。”雷德侯在《万物》中断言,“伏尔泰是在两百年前写下这些话的。也许他并不正确。欲知后事,两百年后再看分晓。”
“你为什么对中国有这样的期许?”本刊记者问。
“因为伏尔泰是两百年前说的,所以,过两百年后再说吧,让时间来判断。”雷德侯答,“我不太清楚一百年以后中国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一百年以后,中国人还在写汉字,写汉字的文化一定是稳定的。”□








